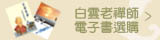禪的智慧 第一集 白雲老禪師著作
攢簇不得
以心繫心,以心住心,心專一故,次第無間,得定心故,心常寂靜──寶雲經。
澧州道行禪師曾說:「吾有大病,非世所醫。」後來有人問曹山:「承古人有言,吾有大病,非世所醫,未審喚做什麼病?」曹山說:「攢簇不得底病!」問:「一切眾生還有此病也無?」曹山答:「人人盡有。」問:「和尚還有此病也無?」曹山答:「正覺起處不得!」問:「一切眾生為什麼不病?」曹山答:「眾生若病,即非眾生!」問:「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?」曹山答:「有!」問:「既有,為什麼不病?」曹山答:「為伊惺惺!」
白雲野語:
攢簇不得,乃是世人通病,惟諸佛為伊,故惺惺不病;吾輩凡聖之間,此病自皈依開始,藉三寶的慈力,早已診治好了,所以,身為佛弟子,無病一身輕,正是修行時節。
大德!教下四眾弟子,雖然環境不同,而道心相同,雖然身份有別,而佛性無異;綜觀近三十年來(以筆者身經體驗),從事正勤精進之修道風氣,的確!出家弟子較為在家弟子來得淡漠,也就是說,在相互的比例上,出家弟子是不夠的,身為人天師範的上座大德們!莫忘記「自度」以「度人」!
識取色空
色顯如夢幻泡影,空寂則真常流露,故說色不異空,空不異色──作者。
有僧問利山和尚:「眾色歸空,空歸何所?」和尚答:「舌頭不出口。」僧問:「為什麼不出口?」和尚答:「內外一如故。」
白雲野語:
不立文字是宗下獨特的風光,所以利山和尚道出「舌頭不出口!」的語句;因為,舌頭若出口,正是文才洋溢,璣珠吐露的時候!果然如此,便形成了句句鏗鏘的篇章了!這便是「內外一如」的結語。
大德!內外一如,不僅是修學應該如此,就是做人處事也應該如此;時下多少「陽奉陰違」的奉迎者,往往表露著「笑面」與「柔聲」去「討好賣乖」,處處「奴顏婢膝」以求歡心。這樣「內外不如」意境,任經無量劫也不會更改;偏於這樣的人,在社會上叫做「下流坯」!在教內叫做「業障鬼」!
人生的短暫,像白駒過隙,誰願意在這樣匆促的生命過程中,做一個下流坯或者是業障鬼呢?
所以說:知色應像夢幻泡影,才能入於真常流露的空寂!
歸去來兮
微妙無相,不可為有,用之彌勤,不可為無;不可為無,故聖智存焉!不可為有,故名教絕焉──肇論。
洛京嵩山和尚,有僧問他:「古路坦然時如何?」他說:「不前!」僧復問:「為什麼不前?」他說:「無遮障處!」老野卻說:「狼虎當道!」
白雲野語:
「古路坦然時境異,今路現前境不同;何如根性多分別,莫說此路前不前!」
誰都知道虛空坦蕩無有落腳處,湖海無邊沒有足跡可循。基於此理,在宗下道路實質的指標上,往往比喻為湖海或虛空,雖然無有落腳處,沒有足跡可循;但是,倘能記取菩提般若,便無須辨認翠竹黃花,也就是說,豁然踏上生死之道,便不論它歸去來兮!
大德!相有相無,並不是道理的癥結,有為無為,才是行者的作法;所以,老野在嵩山和尚的「無遮障處」句後,道一聲「狼虎當道」便是這個原故。
緣聚緣散
無因即無緣,無生亦無滅,因緣皆是境,生滅總歸空;無念無所住,真假假亦真,識得生緣法,法爾猶風雲──作者。
有僧問福谿禪師:「緣散歸空,空歸何所?」師答:「某甲!」僧感驚奇,不由「喏?」的一聲,師反問:「空在何處?」僧答:「即請師道!」師說:「波斯吃胡椒!」
白雲野語:何不說:「烏龜吃喬麥?」亦如空歸何處,回答說是「某甲」一般;蓋烏龜吃喬麥,糟蹋的比吃的多,在歇後語中,稱之為「糟蹋糧食」!此語雖是俚俗言句,但正像是饅頭與麵包,畢竟滋養無別。大德!或者要問,空歸何所,谿禪師說波斯吃胡椒,為何不作正面回答,盡攬一些俚俗語?如此便是所謂的禪麼?
在禪的境域中,事實上就是「塵境」生活的實際體驗;六祖能大師說:「佛法在世間,不離世間覺。」所謂世間,便正是塵境,於諸塵境中的變化,加以觀察體驗,毋容置疑地便能知道「烏龜吃喬麥」,並不是說「糟蹋糧食」那樣 簡單,亦如「波斯」與「胡椒」的答案;應當識取「緣」與「空」在變化中的「緣生緣滅」是「聚散」的真實義論。
樂法不厭
若樂聞法而不厭足者,悟不可思議法──華嚴經。
湖南如會禪師住持東寺時,有人問師:「某甲擬請和尚開堂,得否?」師答:「待你將物裹石頭煖即得!」彼無語,後藥山代替著説:「石頭煖也!」
白雲野語:
好一個游手好閑人物!要求開堂豈非是無事找事?睜著眼將「屎橛」投向大海,卻又請求派艘大船,幫著去海底尋撈取,難怪會禪師要說「裹石頭」言句!
大德!澄水難收,誰令潑水?既然潑了,何必追究;凡事如果事先多予思慮,待到利與弊的認清,然後付諸實施,便不會有甚麼懊喪或苦惱了。
以人生的論值來說,要想得到豐碩的收穫,必須投下有效的耕耘;所謂「有一份耕耘,才有一份收穫。」天底下無有不勞而穫的果實,尤其是「守株待兔」的行為,那不啻是希冀天上掉下饅頭來。
修學的行者!樂法不厭,終有悟期,頓然徹悟,大事圓滿,莫做游手好閑人物!
標立惑人
佛本是自心作,那得向文字中求──寶誌。
僧問虔州處微禪師:「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,與祖師意為同為別?」師說:「恁麼則須向六句外鑒,不得隨他聲色轉!」僧問:「如何是六句?」師答:「語底,默底,不語,不默,總是,總不是,汝合作麼生?」
白雲野語:
「離言捨句是體,窮身究色是用,組合則成魔說!」所謂六句,四句,無非是塵境中事!但,饑餐倦息,循環交替,任管是體也好,用也好,都是不可否認的生活變化;而生活於塵境中,如此變化是必然發生的事實,惟有於此事實中去「疑、思、悟」才得「自心現量」和「意識無染」,否則,教禪有別,有無分明!
大德!參起念止,念起參休,都是修道行者的障礙;如果理會了「聚合」與「生滅」的奧秘,必然識得禪教之根源。所以,老野認為理不可言喻,法不可分別,瘦馬常能馳騁千里,參念輒使「神識」迷濛;基於不為標立所惑,管他是禪是教!故說:
「是佛是心,非心非佛,不是心不是物!」
會麼?教?禪?...。
聖賢僧伽
一切法性常空寂,無有一法能造作──華嚴經。
嵩嶽墮和尚不詳名氏,言行叵測,時山塢有廳甚靈,殿中唯安一 ,遠近祭祠不輟,烹殺物命甚多;一天,墮和尚領侍者行至廟堂,以手杖敲 三下說:「咄!此 只是泥瓦合成,聖從何來?靈從何起?恁麼烹宰物命?」語畢,復擊三下, 乃傾破墮落,未久,有一人,青衣峨冠,忽然跪拜於和尚前;墮和尚見狀問道:「你是什麼人?」其人回說:「我是此廟 神,久受業報,今蒙和尚開導,說無生法,已得解脫,生往天道,故而拜謝。」墮和尚回說:「是你本有之性非吾強言所至!」神再拜而沒。
白雲野語:
世人所謂的迷信,事實上還是由人而起,為人自作;亦如廟中 神,原本泥瓦合成,組之為 ,此泥此瓦,由何而來?緣何而成?無可否認的一切來自人的因緣造作,甚而至所謂靈明,烹宰物命,無一件是出自 神的本身。
大德!難怪墮和尚要說:「聖從何來?靈從何起?」更難得給與我啟示覺路!誠然,是大善知識聖賢僧伽!
版權所有,未經同意請勿任意印製發行
- 禪的智慧第一集 (79K)
相關檔案下載